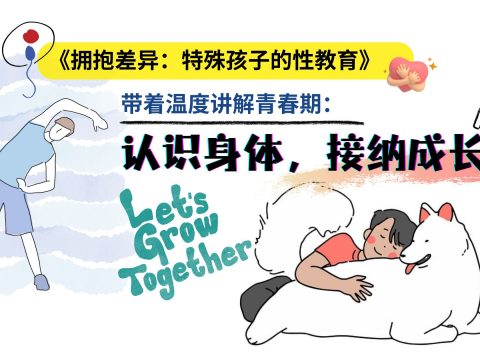一个被性侵的幸存者,从事发到说出口,需要多久的时间?
平均时间 – 23.9 年。
(Australia’s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, 2017)
*****
我今年38岁。我好好回顾我生命的时间线。
7、8岁是案发时我的年龄。
时隔 25、26年,在我33岁时,我上TEDx PS,第一次「公开」演讲。
平均数值是23.9年。我差了一点点。
这25、26年,我为什么不「早」说?
这几年我当其他幸存者的旁听律师,谢谢ta们的信任,ta们常常告诉我ta们的生命故事。
请你听一听,我们为什么不「早」说、「早」报警?
1)我们不知道什么是「性侵」。
因为「性」,很「肮脏」。
没有人没有教过我们身体的界线,身体部位的重要性及自主权。
我们连发生了「性侵」,都不知道,你要我们怎么说?